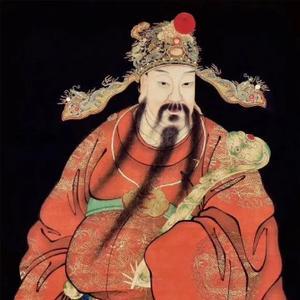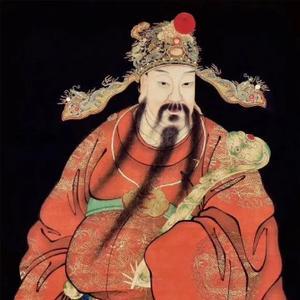
1574820
1977年,李敏在福建龙岩见到了亲姐姐杨月花,不过,杨月花当即向李敏提了一个要求,舅舅贺敏学知道后,说了一句:“和你妈子珍性格一样啊!”
那天百货公司的人不算多,杨月花刚给一位大妈包好布料,一抬头就看见李敏站在柜台边。她认得这几天常来的“领导”,依旧笑着迎上去:“同志要点什么?”李敏没说话,只朝她递了个眼神,孔令华在旁边轻声说:“杨大姐,借一步说话。”
后间仓库堆着些空纸箱,杨月花搬了张凳子让他们坐,自己靠在货箱上,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袖口——那是前几天给邻居家孩子缝书包时蹭的线头,还没来得及洗掉。李敏先开的口,声音压得很低:“大姐,我这次来,是替妈妈……也替爸爸看看你。”
杨月花“嗯”了一声,没接话。她知道对方想说什么,这些天调查组的人早把四十多年前的事掰碎了讲给她听:1929年那个春天,闽西的雨下得特别大,亲生母亲把她裹在红布里,塞给一个姓翁的人家,后来时局乱了,人家怕惹祸,又把她放在了杂货铺门口。她记不得那些了,只记得养母半夜给她掖被角,养父下井回来带的烤红薯,还有矿区大院里孩子们喊她“杨大姐”的声音。
“大姐,”李敏往前凑了凑,眼眶有点红,“北京那边……家里人都盼着你回去看看。妈妈她……”
“不回了。”杨月花打断她,语气平和得像在说今天天气,“龙岩才是我的家。”她顿了顿,看着李敏,眼神清明得很,“我有个要求,你看能不能应。”
李敏赶紧点头:“大姐你说,只要我能做到。”
“别公开我的身份,”杨月花说,“也别跟外面说我是谁家的人。我还是杨月花,百货公司的售货员,郑焕章的媳妇,六个孩子的妈。”她抬手理了理衣角,那身蓝色工装洗得有些发白,却熨得平平整整,“你要是答应,咱们往后还能像现在这样,有空来龙岩,我请你吃客家酿豆腐;要是不答应……”她没说下去,只是笑了笑,那笑容和当年养父从井下上来时,抹着黑灰朝她笑的样子,竟有几分像——都是在苦日子里熬出来的韧劲儿。
李敏愣住了。她来之前想过很多种可能:哭一场?闹一场?或者问为什么当年不要她?唯独没想过是这样一个要求。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外婆说,妈妈贺子珍当年在长征路上,把最小的妹妹留在老乡家,临走前也是这样,只说了句“别让孩子知道她爹妈是谁,安安稳稳过一生就好”。
“大姐,你这……”孔令华在旁边插了句,“这对你不公平。”
“有啥不公平的?”杨月花拿起桌上的账本翻了翻,“我活了四十二岁,没挨过饿,没受过冻,丈夫孩子热炕头,街坊邻居处得像一家人,这日子够公平了。”她合上册子,看着李敏,“你就说应不应吧?”
李敏咬了咬嘴唇,点了头:“我答应你。”
后来贺敏学听李敏讲起这事,在电话里叹了口气:“和你妈子珍一个模子刻出来的!当年你妈带着队伍打游击,敌人围上来了,她把药箱往老乡怀里一塞,自己端着枪就冲上去,说‘别管我,保住药比保住我有用’。这股子认死理的倔劲儿,还有这心劲儿,真是一点没差。”
杨月花后来还是在百货公司上班,每天早上六点起床,给孩子们做早饭,然后骑自行车去单位,站柜台站到晚上七点。邻居张婶有次撞见她给李敏写信,纸上就几行字:“家里都好,小儿子考上矿中了,不用挂念。附了张全家福,后排左数第三个是你外甥,刚学会背《静夜思》。”
有人问她:“知道自己是大领导的孩子,心里就没点想法?”她正纳鞋底,头也不抬:“啥想法?能比我家老头子下井安全更重要?能比孙子孙女喊我奶奶更实在?”
晚年她搬进了矿区新盖的楼房,阳台上摆着养母留下的那盆仙人掌,每年春天都开花。有回电视台来拍纪录片,想采访她,她关着门没让进,隔着防盗门喊:“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,没啥好说的。”
直到她八十八岁走的那天,街坊们来送葬,才发现她衣柜最底下压着个红布包——里面是调查组当年给她的照片,照片上年轻的男人穿着军装,女人梳着齐耳短发,笑得温柔。红布里还裹着半块烤红薯干,硬邦邦的,是养父当年常给她带的那种。
总结:杨月花的一生,像闽西大山里的老茶树,扎根在平凡的土壤里,却长出了最坚韧的枝干。她不要显赫的身份,不贪浮名的荣光,只守着烟火气的日子,把苦难酿成了岁月的甜。这种“认死理”的倔,这份“知满足”的心,恰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品格——平凡,却比金子还闪亮。
信息来源:四川红网:《1977年杨月花见到李敏,事后提出一个要求,贺敏学:和你妈子珍性格一样啊!》